绚烂秋色当共赏(2)
2022-03-12 来源:文库网
秋色绚丽入眼帘,浅黄深金远无边。
恨无画笔巧描绘,枫叶点点衬渔船。
翻看相机里一张张“杰作”,不仅沾沾自喜。有这样如诗如画的秋色做伴还惧怕什么寒冷的冬天?
秋色绚烂
胜丹青,欣赏还需约友朋。
于是我想起老朋友翟兄。说起翟兄,还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交情的起源。1981年1月,我从位于松花江下游的一个林区小镇调入哈尔滨国营香坊木材厂工会做宣传工作。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转轨变型时期的年轻人似乎已经觉察到知识的重要性,大江南北到处涌动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热潮,故而求知上学的热情十分高涨。由于爱好所致,我也报取了哈尔滨业余文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文学青年创办的夜大,主办单位为省文联。地点在位于道里区的哈尔滨第一中学。学校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属于尚未被承认学历的夜大,但师资阵容却令人称叹。聘请的老师均为哈师大、黑龙江大学著名的教授、讲师。他们是逻辑学教授徐国柱、中文系教授刘小南、文学理论教授周蒙等。校长为黑大资深教授陈缇,可谓人才荟萃,名流济济。时任《北方文学》编辑的老作家关沫南先生也曾来校为我们授课。先生身量不高,头留长发,一派儒者风范。语速和缓,亲切慈祥,俨然一位慈爱的长者。他的一席讲座使我们获益匪浅。2007年10月,我去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参加由省医保局组织召开的工作会议,结识了关沫南先生的后人,目前在省文联就职的长子。得知先生已经辞世,不仅深感惋惜。斯人已逝,言犹在耳;风范长存,激励后人。记得著名作家萧军曾在女儿的陪同下,应陈缇校长之约,为我们授课。我们知道萧军曾与我省早期女作家萧红结为伉俪,在我们眼里无疑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因此,他主讲的这堂课格外吸引我们,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他们这些热血青年如何冒着白色恐怖,用革命文化唤起民众来拯救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东北三千里河山;如何运用手中的笔书写进步文章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英雄壮举,令人感奋;悲壮业绩,催人奋起。听着老人的讲述,大家顿觉热血沸腾,礼堂里鸦雀无声,萧老激情苍劲的声音,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屈辱悲愤的峥嵘岁月。萧老年事已高,走路已经拄着拐杖,却能不远千里来到哈尔滨为我们授课,除却他对哈尔滨这个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有着浓厚的感情外,还仰赖于他与陈缇校长之间那种经过生死考验的深厚友谊。课程安排在每周三、五晚上,和周日的上午。很巧的是,翟兄也报了该校,这样我们就不期而遇地成为同学。因此,一到上课时间,我们就一同乘坐工厂的通勤车由香坊来到道里尚志大街。一来二去熟悉了,也就成为要好的朋友。翟兄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善良、真诚、内敛,朴实、不善言表。有道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尔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以及就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进行交流。在文学院的2年间,可谓受益匪浅。我的6篇诗作还被选为优秀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这期校刊至今我保存完好。每当看到纸张已经泛黄的校刊,我就会忆及在文学院就读的情景,以及那些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可亲可爱的师长们。
恨无画笔巧描绘,枫叶点点衬渔船。
翻看相机里一张张“杰作”,不仅沾沾自喜。有这样如诗如画的秋色做伴还惧怕什么寒冷的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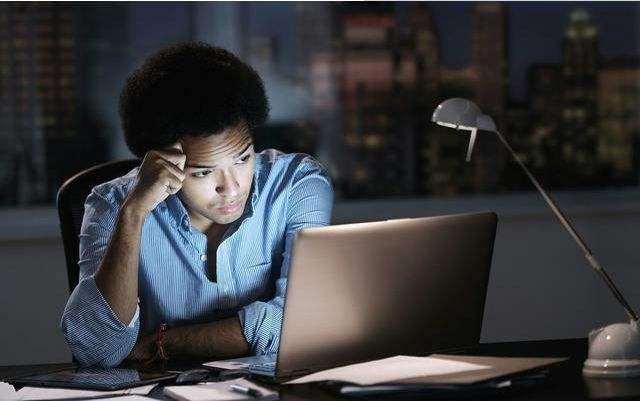
秋色绚烂
胜丹青,欣赏还需约友朋。
于是我想起老朋友翟兄。说起翟兄,还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交情的起源。1981年1月,我从位于松花江下游的一个林区小镇调入哈尔滨国营香坊木材厂工会做宣传工作。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转轨变型时期的年轻人似乎已经觉察到知识的重要性,大江南北到处涌动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热潮,故而求知上学的热情十分高涨。由于爱好所致,我也报取了哈尔滨业余文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文学青年创办的夜大,主办单位为省文联。地点在位于道里区的哈尔滨第一中学。学校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属于尚未被承认学历的夜大,但师资阵容却令人称叹。聘请的老师均为哈师大、黑龙江大学著名的教授、讲师。他们是逻辑学教授徐国柱、中文系教授刘小南、文学理论教授周蒙等。校长为黑大资深教授陈缇,可谓人才荟萃,名流济济。时任《北方文学》编辑的老作家关沫南先生也曾来校为我们授课。先生身量不高,头留长发,一派儒者风范。语速和缓,亲切慈祥,俨然一位慈爱的长者。他的一席讲座使我们获益匪浅。2007年10月,我去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参加由省医保局组织召开的工作会议,结识了关沫南先生的后人,目前在省文联就职的长子。得知先生已经辞世,不仅深感惋惜。斯人已逝,言犹在耳;风范长存,激励后人。记得著名作家萧军曾在女儿的陪同下,应陈缇校长之约,为我们授课。我们知道萧军曾与我省早期女作家萧红结为伉俪,在我们眼里无疑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因此,他主讲的这堂课格外吸引我们,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他们这些热血青年如何冒着白色恐怖,用革命文化唤起民众来拯救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东北三千里河山;如何运用手中的笔书写进步文章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英雄壮举,令人感奋;悲壮业绩,催人奋起。听着老人的讲述,大家顿觉热血沸腾,礼堂里鸦雀无声,萧老激情苍劲的声音,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屈辱悲愤的峥嵘岁月。萧老年事已高,走路已经拄着拐杖,却能不远千里来到哈尔滨为我们授课,除却他对哈尔滨这个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有着浓厚的感情外,还仰赖于他与陈缇校长之间那种经过生死考验的深厚友谊。课程安排在每周三、五晚上,和周日的上午。很巧的是,翟兄也报了该校,这样我们就不期而遇地成为同学。因此,一到上课时间,我们就一同乘坐工厂的通勤车由香坊来到道里尚志大街。一来二去熟悉了,也就成为要好的朋友。翟兄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善良、真诚、内敛,朴实、不善言表。有道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尔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以及就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进行交流。在文学院的2年间,可谓受益匪浅。我的6篇诗作还被选为优秀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这期校刊至今我保存完好。每当看到纸张已经泛黄的校刊,我就会忆及在文学院就读的情景,以及那些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可亲可爱的师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