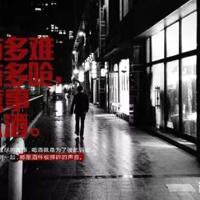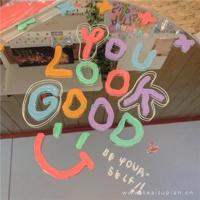眼泪和局外人——加缪的《局外人》
2022-03-11 来源:文库网

原创:咖啡公子——墨涵 寒假里,向儿子推荐了一本书——加缪的《局外人》。 谈及加缪,爱好文学者应当不会陌生。作为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他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他才44岁。 加缪的往往富于哲学的色彩,或者说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他的笔只在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主要代表作为《局外人》和《鼠疫》,其中《局外人》更是享誉世界。 《局外人》塑造了默尔索这个“局外人”形象,他的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加缪想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去揭示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加缪了,在完成《局外人》时,不过才26岁。 开卷有益,这本书的主要意义,儿子应该是读懂了。他在学校的写作练习中,把读书体会写了下来,成了稿。感谢老师的鼓励与赏识,给了儿子机会,以此稿参加学校关于读书活动的,这篇演讲稿名为《眼泪和局外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具体哪一天,我说不清。” 这是加缪《局外人》的开头,也是主人公默尔索的自述。他收到电报后,对自己惟一的亲人——母亲的过世竟漠不关心。 在母亲的葬礼上,萍水相逢的人嚎啕大哭,身为儿子,他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后来,他误杀了人,上了法庭。审判席上,检察官把杀人和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联系起来,指控他曾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他的母亲”,指控他麻木不仁,毫无人性,没有灵魂,是有预谋的杀人。而他从头到尾没有为自己做一点辩护,仿佛这是对别人的审判,而他,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终于,默尔索被斩首示众,而置于他死地的根源是——他没有在母亲的墓前流下眼泪。 可他真的是一个残忍的人吗?不,他不但不残忍,更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只是在真诚地爱着一个同样真诚的世界。 他在母亲的墓前无动于衷,是因为他确实哭不出来。对于一个成年人,还要应付着继续,而母亲,也在死前的那一刻得到了解脱。就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哭她”。可是,他的这种“庄子击鼓”的心态,又有多少人可以懂?而别人为母亲所流下的泪水,真的是实心实意的吗? 人们在各个场所常常都需要流泪。当政治家发表的演讲时,人需要热泪盈眶,表明自己对他的观点感同身受;当参加某位亲友的葬礼时,远亲们需要嚎啕大哭,体现出自己悲痛欲绝,有情有义;当参观苦难博物馆时,即使自己并不想哭,参观者也要假惺惺地挤出眼泪,不舍得擦,甚而在脸上抹开。他们好像在说:我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若吝啬眼泪,必将遭到别人的误解和白眼。 这种迎合大众的现象,被称之为“媚俗”。然而,从古至今,媚俗从来不是什么鲜见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框架,人类所有的博爱,都是建立在这种泪水的基础上的。 但是,那些看透了社会本质,不愿流下媚俗的眼泪的人,就真的有罪吗? 是的,对社会来说,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的理性无法被道德观念所接纳。 就像默尔索,他不是白痴,不是混蛋,不是冷血动物,他只是理性到不屑于戴起面具,在世俗中行走的局外人。 局外人,有着自己的价值观,游离在媚俗之外,却被哪些所谓自认为有正确三观的人唾弃。人们总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自以为是地抓住个体的孤独另类的弱点进行审判,也正因为这种不容异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局外人的悲哀。 面对“不流泪既是罪过”的世俗道德体系,我们在众人都哭时,是否应当允许有的人不哭?尤其“哭”已经成为一种表演时,是否更应当允许有人不哭?在生活中,我们是否只能做个两面人,在自己真实的外表上覆盖上一层虚薄的假象? 也许,真实的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局外人。而社会,是否应该给那些理性的局外人留下至少生存的空间呢?” 此时,估计儿子已经上了台,开始了他的这篇演讲,这样的经历儿子并不多,紧张是在所难免的。 之前,大道理我也没去多说,理论的东西说多了反而无益。其实,能够站在演讲台上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因为,经历才是人成长的最佳途径。而“重在参与,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道理,随着儿子的渐渐长大会懂。 最近,我的杂事事依然较多,每天也总觉得有点累。今天,挤出了仅一小时时间简单地就聊这么多。 也许,儿子放学回来会让我删了这篇文,因为他曾向我提过建议,尽量不要在我的文中提及他。我也赞同,这是他的权利。此时,我暂不管那么多,先发出去。如果儿子觉得不妥,我再另行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