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宜读书
2022-03-11 来源:文库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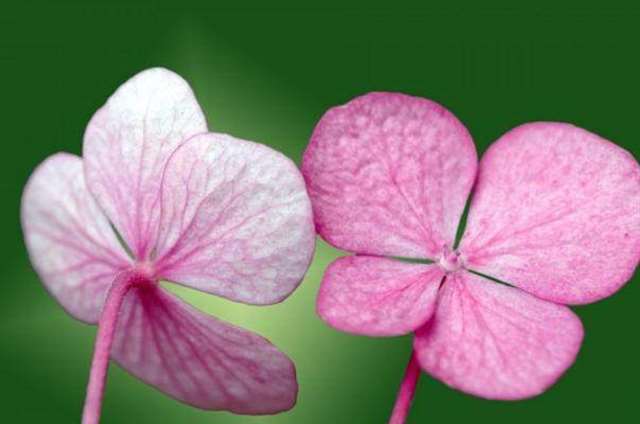
夜间大雨,驱走热浪,窗外凉风阵阵,正宜读书。 对于书痴来说,一日忙碌之后,夜间读书,最惬意不过。而若读书不得法,读得发腻,昏头胀脑,也添苦恼。 读书之法,因人而异,而我自有妙法,那便是杂而览之——把五六本书放在床头,每本只读一小段,费时约半小时,如此读来,二小时可读四本,不仅不腻,而且每本书都留个悬念,下一晚读书,都有急不可待之感。 今夜所读,第一本书是《废名选集》。 废名,"京派文学"鼻祖,师从周作人,对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影响颇大,然而,今人多不识,莫怪大众,恰如林语堂、胡适等,队站错了。 废名风格独特,呈"散文化",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正如废名自称——“有唐人绝句的特点”。 今晚看的,是他的《浣衣母》,文中母亲是李妈:“这茅草房建筑在沙滩的一个土坡上,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李妈的李爷,也只有祖父们知道,是一个酒鬼;当李妈还年轻,家运刚转到菱滞的时候,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留给李妈的:两个哥儿,一个驼背姑娘,另外便是这间茅草房。李妈利用这天然形势,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 李妈很年青就守了寡,带着两儿一女,在清贫中矢志守节,又为人谦抑,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母。 然而,她内心的痛苦和孤独,别人很难知。 一直,她有个梦支撑着,高大瓦房,在丈夫手上消失,她希望在儿子手上恢复起来。可是,两个儿子却不争气,长大后,一个死了,一个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当兵去了。后来,唯一与自己相伴的驼背女儿——也死了,梦,彻底碎了。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爱他的人,一个比她大儿子大四岁的中年汉子。她想按照自己的情感方式,于是,她迅速地失去了人们的敬仰,又被迫和中年汉子分开。 人们对李妈的尊敬,构成了集体专制,把李妈推到祭坛,作了牺牲。 都说,人只要走好自己的路,莫管他人怎么说,可是谁能逃脱时代的枷锁、世俗的眼光? 再读的是一本《宋史》,这是一部断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振是宋史大家,师从邓广铭。 今晚所读只是其中一段——“宋初宫廷内部的斗争”。 “烛影斧声”,这是段老历史,但原来史书循旧例,总把这段历史定性为千古疑案,而陈老断定毫不含糊——公元976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夜,赵光义杀死了病重的哥哥宋太祖赵匡胤,夺了皇位。陈老这态度,我喜欢。 宋太宗赵光义是个真小人。 他登基以后,为了掩盖弑兄真相,联合原丞相赵普,编了个“金匮之盟”的,伪证他是遵循母亲杜太后之意,才继承帝位。 杜撰的继承顺序为:大儿子赵匡胤——二儿子赵光义——三儿子赵廷美——赵匡胤的大儿子赵德昭。 而待帝位稳固后,赵光义便先后把三弟赵廷美、大哥的两个儿子赵德芳、赵德昭,逼贬而死。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在利益面前,莫高估了道义与情义的价值,就算也会变得苍白无力。 《岁朝清贡》是我今晚读的第三本书,汪曾祺所著。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这段文字来自《葡萄月令》,葡萄就像个大老爷,呆在架子上。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来自汪老的《夏天》。 在汪曾祺的文字中,总有一种平淡的美,平淡中有着清茶的味道,又有一种细水悠悠的淡雅,淡雅中带着袭袭清香,让人久久回味。 平淡而真诚的语言,往往最有魅力。因为,深厚的感情,丰富的思想,都包含其中。 看完清新的散文,又读了一则小古文。 一则是《一举而三役济》,来自沈括的《梦溪笔谈》: 主人公丁谓,是宋代的名臣,奉命主管修复被烧毁的宫室。 但是取土很远是个困难,丁谓就命令工匠在大街上挖土。 没过几日,大街就成了深沟。 丁谓又命令工匠,把汴河河水引进沟中,再顺着沟中的水,把修缮宫室要用的材料运进宫中。 宫殿修完后,丁谓再下令,把废弃的砖瓦、灰土等填到深沟里,又把它恢复为街道。 开沟注水、水运资材、填渠成街,一举多得,为政府剩下巨额费用,丁谓真是聪明绝顶,能臣典范。 关于丁谓,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溜须》。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寇准,没错,就是那位在《杨家将》中为老杨家平反伸冤的那位双天官。 寇准做宰相时,觉得丁谓不错,就把他引进入中枢,做了副宰相。 有一日,中书省聚餐,寇准不注意,一点汤汁流到胡须上了。丁谓忙上前给他抚去(溜须)。 寇准是个直肠子,冷了脸:"一个副宰相,给上司溜须,成何体统?“从此,丁谓恨上了寇准,投靠了了刘皇后,构陷寇准,将寇准出知相州,一直贬到雷州半岛,最终死在了那里。 无德的人,智商越高,杀伤力越大,一点也不假。努力做个君子,但是,小人,不可不防。 临睡前,我又捧起了韩少功的书。 谈起韩少功,《爸爸爸》是他的成名作,也是现文史中“寻根小说”的代表作。此外,他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都是经典。 今晚我读的《归去来》,是他的短篇,一篇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 小说内容并不复杂: 一个叫黄治先的“我”,神使鬼差地来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是,在“我”记忆中,从没有来过这儿,也不知道这儿的地名,不认识这儿周围的人。 熟悉的是,“我”似乎又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是矮矮的牛房前“有个歪歪的麻石椿臼,那臼底的泥沙和两片落叶,都似曾相识”。 更为怪异的是,这里的人们似乎个个都认得“我”,并且把“我”当成了“马眼镜”——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 在和那些自认为认识“我”的人聊的过程中,“我”慢慢知道了:那位“马眼镜”曾经在这儿当过民办教师,好像还因为拒绝过一个姑娘朦胧的,而导致了姑娘的不幸;“我”还和眼前的这个叫艾八的人一起打过猎;好像还杀了一个村里叫“阳矮子”的无赖,为此甚至坐过大牢? 晚上,“我”洗澡,朦胧间觉得自己小腿肚上的那个伤疤,是被一个叫什么矮子的人咬的,自己当时用一根牛绳勒死了他…… “我”恍惚起来,真实地感觉到,马眼镜”的灵魂在自己体内渐渐复苏。 慌乱地逃回旅社,“我”拨打了远方一个朋友的电话。电话那头称呼“我”为“黄治先”。“我”愕然了,“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么?”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寻根文学作品。家园是根,传统是根,无论多少年过去,曾经的某段岁月,早已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令我们梦回牵绕,无法释怀。 此时,已近23.30了,该睡觉了,蔡崇达的《皮囊》明天再读吧......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昨日,一位同学取笑我,他笑我如今毫无审美观,而我似乎并没反驳,只是呆呆地想事儿,现在,也在想着相同的事儿—— 那套十本的《清代全史》正在路上,估计,明天,那美丽的身影就可以抵达南京了........ 原创:咖啡

























